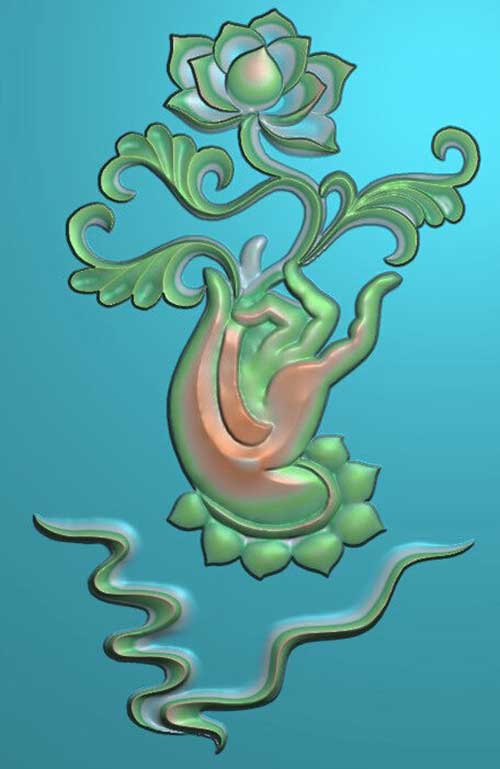清实贤(莲宗十一祖)
实贤,字思齐,号省庵,是常熟时氏的后人。从小不沾荤腥,出家后,参“念佛者是谁”,有省悟,说:“我梦醒了。”闭关在真寂寺三年,白天阅览藏经,晚上念诵佛号。到鄮山礼拜阿育王塔,曾经在佛的涅槃日,大力召集信众,广修供养。在佛前燃指,发四十八大愿,终于感应到舍利放光。作《劝发菩提心文》,激厉四众,读诵的人多有读到痛哭的。那文章说:“曾经听说入道的要门,发心为第一;修行的急务,立愿为首要。愿立下那众生可以度;心发起那佛道才能成。如果不发起广大的心,立下坚固的愿,那纵然经过无量的劫,也依然还是在轮回,虽然有点修行,总是徒劳辛苦。所以《华严经》说:‘忘失菩提心。修诸善法。是名魔业。’忘掉菩提心尚且是魔业,何况没有发菩提心呢?所以知道要想成佛,必先具备发菩萨愿,不可延缓啊。但是心愿的差别,那现出的相就多了,现今为大众略说一说。相有八种,所谓邪、正、真、伪、大、小、偏、圆。世上有那种修行人,修行总是,不深究自心,只是知道外面的事务。或者追求利养,或者喜好名闻,或者贪图现世的欲乐,或者奢望未来的果报,这样的发心,就叫做邪。既不追求利养名闻,又不贪图欲乐果报,只为解脱生死,证悟菩提,这样的发心,就叫做正。每一念都是上求佛道,每一心都是下化众生,听到佛路长远,不会退却;看到众生难度,不会厌倦。就如登上万仞的高山,必须终极山顶;就如登上九层的高塔,必须直奔塔颠,这样的发心,就叫做真。有罪不忏悔,有过不消除,内在浊外在清,开始勤苦最终懈怠,虽然有好心,但被名利所夹杂;虽然有善法,但被罪业所染污,这样的发心,就叫做伪。众生界度尽,我的愿才尽;菩提道达成,我的愿才成,这样的发心,就叫做大。观察三界如牢狱,看待生死如怨家,只期望自度,不想度他人,这样的发心,就叫做小。若是在心外认为有众生,以及佛道,愿意度脱愿意成就,功勋不忘,知见不灭,这样的发心,就叫做偏。知道自性是众生,所以愿意度脱;自性是佛道,所以愿意成就,不见任何一法离开心却另有。以虚空的心,发虚空的愿,修虚空的行,证虚空的果,也没有虚空的相可得,这样的发心,就叫做圆。知道这八种差别,就知道审察;知道审察,就知道去掉和取得;知道去掉和取得,就可以发心。什么是审察?就是我的发心,在这八种中,是邪是正?是真是伪?是大是小?是偏是圆?什么是去掉和取得?所谓去邪,去伪,去小,去偏;取正,取真,取大,取圆,这样的发心,才能叫做真正发菩提心啊。这菩提心,是善法中的王,必须因缘,才能发起。现今说因缘,大概有十种,是哪种十种呢?一者,念佛的重恩。二者,念父母的恩。三者,念师长的恩。四者,念施主的恩。五者,念众生的恩。六者,念生死的苦。七者,尊重自己的灵性。八者,忏悔业障。九者,求生净土。十者,为了使正法能久住。为什么说念佛重恩?因为我释迦如来,从初发心,为了我等众生,行菩萨道,经过无量的劫,受尽各种苦。我造业时,佛就哀怜,方便教化,而我愚痴,不知信受。我堕地狱,佛更悲痛,要代替我受苦,而我业重,不能救拔。我生人道,佛用方便,使我种善根,世世生生,追随着我,时刻不忘我。佛最初出世,我还在沉沦,如今我得人身,佛已经灭度,什么罪让我生在末法?什么福让我能出家?什么障碍让我不见金身?什么幸运让我遇到舍利?这样的思惟,如果过去没种善根,怎么能听到佛法?听不到佛法,哪里知道常受佛恩?这个恩这个德,高山难以比喻。自己不发广大心,行菩萨道,建立佛法,救度众生,纵然是粉身碎骨,岂能报答?这是发菩提心的第一因缘啊。为什么说念父母恩?因为哀哀父母,生我辛劳,十月怀胎,三年乳哺,才能成人,指望继承家风,传承香火。但如今我等已经出家,就叫做释子,衣食不供给,祭拜也不管,活着不能赡养他们的身体,死后不能引导他们的神灵。对世间就是大损失,对出世又没有实益,两方面都有失掉了,重罪哪里逃?这样的思惟,只有百劫千生,常行佛道,十方三世,普度众生。那么不只是一生的父母,而是生生世世的父母,都得到救济。不只是一人的父母,而是人人的父母,都可以超升。这是发菩提心的第二因缘啊。为什么说念师长恩?父母虽然生育我的身体,若是没有世间的师长,就不知礼义;若是没有出世的师长,就不解佛法。不知礼义,就同异类一样;不解佛法,就跟俗人有什么不同?如今我们大概知道礼义,略微了解佛法,袈裟披盖形体,戒品沾贴身上。这样的重恩,从师长那里得来,若是求小果,仅仅能够自利,如今为大乘,普愿利益他人,那世出世间的二种师长,都能得到利益。这是发菩提心的第三因缘啊。为什么说念施主恩?因为现今我们日常费用,并不是自己已有的。三餐的粥饭,四季的衣裳,疾病须要医治,身体耗费,这些都是出自他力,拿来为我所用。他是竭力耕种,尚且难以糊口;我却安坐受用,还觉得不称心。他是纺织不停,还是依旧艰难;我却衣服有余,哪里知道爱惜?他是草门蓬屋,困扰终身;我却广厦闲庭,游乐一世。用他的劳苦,供养我的安逸,心里能安稳吗?拿他的利益,滋润自己的身,合乎道理吗?自己不是悲智双运,福慧都庄严,使信众受恩,众生受益,那一粒米一寸丝,就要偿还有分了;地狱饿鬼,就要恶报难逃了。这是发菩提心的第四因缘啊。为什么说念众生恩?因为我与众生,从旷劫(无量劫)以来,生生世世,互相做过父母,彼此有恩情。现今虽然隔世昏迷,互不相识,按理推论,能不报效吗?如今那披毛戴角的动物,怎么知道不是昔日做过它们的子女呢?如今那蠕动蜎飞的昆虫,怎么知道不是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呢?甚至那呼号在地狱下的,挣扎在饿鬼中的,苦痛有谁知道,饥寒向谁倾诉?我虽然见不到听不到,他们必有求救求济,不是经过的不能说这事,不是佛不能说这话,那有邪见的人,怎么能知道这些呢?所以菩萨观察到蝼蚁,都是过去的父母,未来的诸佛,常想利益它们,念念要报它们的恩。这是发菩提心的第五因缘啊。为什么说念生死苦?因为我与众生,从无量劫以来,常在生死轮回,不能解脱。人间或天上,这里或他方,出没有万端,升沉只片刻。黑门(地狱)早上出去晚上就回来,铁窟(地狱)暂时离开很快又进入。登上刀山,就是身体无完肤;攀上剑树,就是寸心都割裂。热铁不管饱,吞下去肝肠尽烂;洋铜不止渴,喝下去骨肉粉碎。利锯肢解(刀锯地狱),断了再续接;巧风猛吹(地狱业风),死了活过来。猛火城中(猛火地狱),忍心听那鬼哭狼嗥的惨叫?煎熬盘里(煎熬地狱),谁来闻那痛苦不堪的呻吟?冰冻刚刚凝固(冰冻地狱),那像青莲结蕊;血肉已经分裂(分裂地狱),身如红藕华开。一夜间的生死,地下常常经过一万遍;片刻的苦痛,人间已过百年了。频频劳烦地狱的鬼差,谁信阎罗老翁的教诫。受地狱罪罚时知道苦,虽然悔恨怎么么来得及?脱离地狱还是遗忘,那造业也依旧如故。心没有恒常的主人,类似商家而到处奔忙;身没有固定的形体,好像房屋而频频搬家。大千世界无量劫,难以穷尽有多少轮回的身;四海翻腾的波涛,谁计算得清生死别离的泪?累累堆积的白骨,超过那高山;茫茫无边的横尸,多过那大地,假使不听到佛的话语,这事谁能见到谁能明白?没有看到佛经,这理怎么知道怎么醒觉?那就像先前一样贪恋,仍旧痴迷,但只恐怕是万劫千生,一错百错。人身难得而容易失掉,时光过去而难再追回。轮回的道路迷茫,生死的别离长久。三途的恶报,还是自己承受,痛得说不出来,谁能代替呢?所以应该断掉生死的河流,出离爱欲的大海,自己和他人都得救济,一同登上解脱的彼岸,无量劫以来最殊荣的功勋,在此一举。这是发菩提心的第六因缘啊。为什么说尊重己灵?因为我们现前这一心,当下与释迦如来没有分别。那为什么说世尊无量劫以来,早已成就正觉,而我等昏迷颠倒,还是凡夫呢?再说我世尊具有无量神通智慧,功德庄严,而我等只有无量业力紧系的烦恼,生死缠缚,心性是一样的,但迷和悟有天渊的差别。譬如无价的宝珠,埋没在淤泥里,就当作瓦砾,不加爱重。所以应该用无量的善法,对治烦恼,修德有功效,性德才能显现。如宝珠被洗净,悬挂在高处,光明透亮,映照一切。才能不辜负佛的教化,不辜负自己的灵性。这是发菩提心的第七因缘啊。为什么说忏悔业障?经上说:“犯一吉罗(很轻的一种罪),如四天王寿五百岁堕泥犁(地狱)中。”吉罗小罪,尚且有这样的果报,何况重罪呢?那果报就难说了。如今我等平常日用中,一举一动,常常违戒律,一餐一水,频频犯尸罗(戒)。一天犯的戒,就是无量无边,何况终身多劫呢?所造的罪,更是不可说了。就拿五戒来说 ,十人就有九人犯,显露的少隐藏的多。五戒名叫优婆塞戒,尚且不能完全具足,何况沙弥比丘菩萨等戒呢?又不必说了。若不痛心自己和他人,悲叹自己和他人,身与口都真真切切,声泪俱下,为普遍众生,求哀忏悔,那千生万劫,恶报难逃。